#历史开讲# 古代史研读:元朝时期,欧洲游历者笔下的江南社会小人物——在欧洲游历者笔下还描绘了许多不同类型、不同身份的江南人,尤以《马可·波罗行纪》中的描写居多,以商人的视角更易切入到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体味江南的世俗生活。
相比较而言,传教士马黎诺里和鄂多立克就显得有些拘谨和放不开,接下来便集中解读《马可·波罗行纪》中那些特别存在的小人物 占卜吉凶的星者 《马可·波罗行纪》中特别提到当地民俗“信星者之说甚笃”书中共有两处记载,具体阐述两点问题:一是星者在何处,在街道之中以及市场周围;二是星者的主要职责有何,星者主要为儿童出生、商业贸易、外出旅行、举行婚礼等占卜吉凶,因为时常占卜很准确,故而城中有很多人愿意相信。

这里又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马可·波罗对宋元时期杭州当地“星者”和占卜习俗的描述之真实性究竟如何?其二,为何马可·波罗会关注“行在”城市的这一侧面?游记中对“星者”的分布作出了说明,原文提到的“其他街道居有医士、星者”中的“居”,并不必然是“居住”义, 应是指杭州城内求医或问卜的某些专门市场,而非其人集中居住之坊巷。
追溯到史书中,宋人张端义《贵耳集》谈及在临安的中瓦“天下术士皆聚焉”,《西湖老人繁盛录》中也有记“卦山卦海(中瓦)”,可见其时杭州城规模最大的卖卜市场,就是坐落于御街旁的中瓦除中瓦外,城内各处市集还聚集有大批以卖卜算命为生的术士,这在《梦粱录》中也有明确记载。
马可·波罗在第二处关于“星者”的记载中也指出“此种星者,在一切市场为数甚众”,这一描述也极为契合《西湖老人繁盛录》《梦粱录》等记载的卖卜者既相对集中又分布各处的杭州街市情景因此,马可·波罗所观察到的这一细节是十分适合其时的社会情态。
《行纪》的第二处记载更多描述了杭州民间的命理信仰和这种信仰在百姓日常生活中,主要集中在出行、婚媾和经商等方面的具体表现

在宋元时期就有“卜行择吉”的习俗,《梦粱录》就提到要定帖,其实帖中需明白要写的多项内容,就包括了男女双方的“年甲月日吉时生”,也即马可·波罗提到的“出生之日、时、刻”同样,元代留下来的求卜资料,在流动性欠活跃的近古社会,的确颇与商人关系密切,须长途旅行、贩运货物的行商问卜是他们应对变化莫测的商业风险的一种方式。
高丽刊行的汉语整科书《旧本老乞大》模拟了商人结束生意准备启程归国前的一段经历,所言虽不是杭州城,却颇为生动地再现了马可·波罗描述的求卜者携带八字生肖之记录“往叩星者,预卜吉凶”的场景 马可·波罗对“行在城”中众多“星者”以及占卜风俗的关注,并不是纯粹的偶然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可·波罗行纪》另一处,他对“汗八里”的“星者”也有过浓墨重彩的描述,这处记载出自《马可波罗行纪》第103重章“汗八里城之星者”,马可波罗两次提到星者及其占卜的地点,同属宋元之际地位特殊的大型首都城市,这一点绝非偶然。

从风俗史的角度看,杭州城市中占卜术大受欢迎,仿佛是一种内生的、“自然”形成的地方风气 但针对此种社会风俗,更倾向于将之视为一种特定时代和特定地域发生的经济社会现象其一,它意味着人口,尤其是一种职业人口的流动。
马可·波罗或行在城风俗的其他目击者和记录者所共同观察到的,提供拆字、相面、八字和星命等占卜服务的大规模术士群体,并不是一种城市内部世袭的、固化的阶层,而是处于流动和更新的状态其二,它同时意味着城市中存在着庞大的占卜消费群体。
据史料记载,占卜业的消费群体上至皇亲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等各个阶层且普遍分布在杭州城内,这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个城市各阶层居民的某一类心理状态——承受各自生存本身带来的心理压力,这需要通过某种途径得以宣泄和安慰, 这或许就是“行在城”的“城市生态”离不开术士群体和卖卜业的深层次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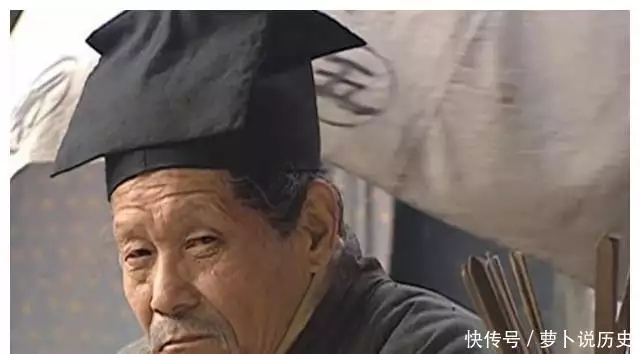
马可·波罗在《行纪》中同时提到“行在城”和“汗八里”的“星者”必然不是偶然,在游历东方的道路中,他已经敏锐捕捉到了城市间的相通性,以异域人的视角连接东方城市间的内在联系,这背后存在着与社会经济变迁密切相关的时代因素,基于此,马可·波罗的中国印象在逐步加深,中国版图中形态各异的地域形象也在游历途中一一浮现。
香艳妩媚的娼妓 随着元代经济的繁荣,元代的娱乐行业不断发展起来,城市的手工业、商贸经济的繁荣为元代娱乐活动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助推对娱乐生活的渴求,而作为娱乐行业组成部分之一的娼妓服务业也随之发展起来。
在中国南北方各地都普遍存在着娼妓服务行业,且体量非常大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就有关于元大都中“卖笑妇女”的描写,她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城中对于其居住地也有相应管制,她们被要求不得居住在城内,只能居住在城外。

同时对于娼妓也有诸多管理事项记录在刺木学本第二卷第七章中,具体办法是以逐级分管的方式进行,新旧城共有两万五千名娼妓,有一名官吏总负责,在其下又设管理百人千人左右的官吏,他们全部隶属于统一主管者 之所以这样管理的原因书中也有提及,是因为有很多外来使者来到元大都觐见朝拜,需要以此为欢迎仪式来款待他们。
同时要求主管人员每晚为外来使者以及相关陪同人员配有一名娼妓,每晚更换并且不收取留宿的费用,只把这部分收入作为娼妓应当缴纳给大汗的税金 这里描述娼妓人数的数字不一定可靠,但是元大都有大量娼妓存在却是事实,从设有专门负责的官吏进行管理便可知娼妓数量定不在少数。
元大都是如此景象,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尤其在富庶的江南地带,当地游手好闲之徒大多喜欢留恋在勾栏瓦肆之间,寻找娼妓陪同玩乐

马可·波罗也在《行纪》中特别提到行在城的娼妓,花花世界迷乱了马可·波罗书中不仅有对娼妓服装打扮的描述,更有外国使臣深陷其中的典型案例,他说到:“这里娼妓的数量非常庞大,已经到无法言说的地步,不仅仅在市场附近能看到很多,在整个城市中都流动着她们的身影。
她们穿着的服饰华丽富贵,身上有迷人的香气,从身边经过能够闻到浓浓的香味 她们身边伺候的仆人也很多,所居住和使用的都十分华丽精美” 马可·波罗感叹从事这类职业的女性擅长魅惑人心,行为举止都极会满足人的欲望,尤其是外国人一旦踏入这类场所,就会沉迷其中,这便更加印证了行在城是欧洲人眼中“人间天堂”的说法。
这里关于行在城娼妓的描述更加细致,和之前所说的元大都娼妓行业很相似,作为一名外国人,马可·波罗记录游历城市中的娼妓时,始终逃离不掉与自身域外人身份相关的场景, 他也极其坦率地谈到行在城不仅因繁华富庶而让人流连忘返,而且有这般香艳的奇遇令人沉醉、无法自拔。

这样的娱乐行为在欧洲人眼中是前所未有的刺激,更让他们感受着东方城市的繁华与自由,他们对娼妓的了解,仅限于走马观花式地观望和体验,但妓女行业背后的故事他们也许未曾深入探寻江南地区的蒙元时期的娼妓无疑是一个特别的女性群体。
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职业,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儒学中“男外女内”的角色分工,而娼妓生活则是一种背离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伦理,某种程度上说,娼妓受社会环境裹挟,社会生活也因娼妓的存在而产生影响 数种皆繁的戍兵 元军按其民族构成进行区分,可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军四种,而在军队的职能上,又分为地方守备军(包括乡军)和守备军。
江南地区,常年驻扎着大量的军队 元代的军队也有不同的兵种,蒙古军、探马赤军主要是骑兵,而汉军和新附军则是步兵 据《行纪》的记载来看,行在城戍兵多以步兵和骑兵居多,军队管理也严谨规范,每年大汗从他众多的臣民百姓中挑选能够手握兵器的人编入军队。

其中还有一项规定是说,从南方征集的戍兵不能驻守所在城市,而是前往外地戍守,戍期三四年结束后才可以调回,这一规定在全国适用总体而言,这里关于戍兵的零星描述只是元代军队建设的冰山一角,但亦足以看出当时社会管理的缜密与严格,尤其对于江南重镇的管控更是高度重视。
马可·波罗和其他前期、后期访华的传教士大不相同,他从商业气息浓郁的威尼斯来到中国,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擅长在国际上航线上进行贸易,以此赚取大量的财富 总的来说,马可·波罗能以一种世故、圆滑的眼光,观察着自己所经过的路线、城市、群体的种种差别。
《马可·波罗行纪》是“物我相合”的经典之作,能够将他者视角的陌生化与对象世界的生动性非常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它不但让中国的风土人情在西方世界流行开来,也深深地影响着西方社会,并促使了整个西方社会文明的变革。